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穿透矿区的薄雾,雾霭像揉碎的棉絮,办公楼崭新的国旗边角被晨风吹得微微卷翘,金线绣的五角星在薄雾里闪着细碎的光。
作为煤矿宣传工作者,我的国庆从不曾在繁华都市的霓虹里度过。这些年,我早习惯了将镜头对准井下千米处的微光——矿灯的光束在黑暗里划出银亮的弧线,照得巷道壁上的煤粒泛着乌润的光,连空气里的煤尘都在光束里跳着细碎的舞;对准矿工黝黑面庞上的汗珠——那汗珠顺着额角的皱纹往下淌,滑过沾着煤灰的颧骨,在下巴尖悬停片刻,才重重砸在工装领口,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;对准传送带旁“保供有我”的红色横幅——横幅边角被井下的风扯得发脆,红色颜料有些地方已被煤尘染得发暗,却依旧像团燃着的火,映得矿工们的眼睛格外亮。此刻,我跟着综采队下井时,胶鞋踩在巷道的碎石上,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轻响,矿灯的光束忽然扫到巷壁上——那面国旗用细铁丝牢牢固定在支架上,红色绸缎被通风口的风吹得轻轻颤动,边角扫过粗糙的煤壁,留下几道淡淡的痕。
“小王,快给我们拍张照!”支架旁,综采队检修班班长老杜粗粝的声音穿透机器的轰鸣。他抬手抹了把脸上的煤尘,掌心的纹路里嵌满了黑灰,却没把脸擦干净,反倒在颧骨处蹭出一道浅白的印子,像幅即兴的素描。工友们闻声围过来,深蓝色的工装沾满了煤屑,肩膀处的补丁被磨得发亮,安全帽上的矿灯拧到最亮,连成一片摇曳的星海。老杜朝我递来一面折叠的小国旗,指尖捏着国旗的边角,指腹因常年握镐头而结着厚厚的茧,连国旗的绸缎都被捏得有些发皱:“把国旗放中间,要亮堂点!”他说着,又往后退了退,把镜头位置让给年轻的矿工小李——小李刚下井两年,脸上还带着青涩,却特意把工装领口拽得整齐些,矿灯的光落在他眼里,闪着紧张又骄傲的光。“按照现在这个进度,今年咱们又能准时完成保供任务,这国庆过得踏实!”老杜的声音裹着机器的嗡鸣,却格外清晰,眼角的皱纹里嵌着细小的煤屑,笑起来时,皱纹像展开的核桃壳,可那双眼睛望向镜头时,亮得像夜空里最亮的星,连煤尘都遮不住那股子劲。我按下快门的瞬间,听见相机“咔嗒”一声轻响,忽然明白,我们记录的从来不是简单的影像——是矿工们掌心的老茧托举的能源担当,是煤海深处,用汗水写就的对祖国的告白。
暮色渐浓时,我坐在办公室整理当天的素材。窗外,矿区的路灯次第亮起,暖黄色的光透过窗户,在桌面上投下长长的光斑。电脑屏幕上,矿工们与国旗的合影格外鲜活,我握着鼠标,指尖划过照片里的国旗,忽然想起下井时,那面国旗在巷壁上飘动的样子,心里满是柔软。文字稿里“保能源安全、庆祖国华诞”的字句,被我反复修改了几遍,每一个字,都像在诉说着煤海的故事。我忽然觉得,作为煤矿宣传工作者,我们的国庆有着别样的意义——我们不是在远方眺望繁华,而是在煤海深处,见证矿工们掌心的温度;我们不是在台下聆听赞歌,而是用笔墨和镜头,将矿工的坚守、煤海的奉献,写成献给祖国的最美诗篇,每一个字,都沾着煤香,每一张照片,都闪着矿灯的光。
夜风吹过矿区,带着淡淡的煤香,从窗户缝里钻进来,拂过桌面上的稿件。我起身走到窗边,望向楼下飘扬的国旗——国旗杆上的绳子被风吹得“哗啦”响,国旗在夜色里展开,红色的绸缎映着路灯的光,像团永不熄灭的火。心里满是滚烫的骄傲,这骄傲,源于矿工们黝黑面庞上的坚毅,源于他们掌心老茧里藏着的力量;源于煤海深处跳动的中国红,源于那抹红在黑暗里,照亮的每一段巷道;更源于我们始终坚信:每一次深入井下的采访,每一次蹲守在传送带旁的等待,每一篇饱含深情的报道,都是在为祖国的发展,注入来自煤海的、最坚实的力量——那力量,像乌金一样厚重,像矿灯一样明亮,更像煤海深处的中国红,永远热烈,永远滚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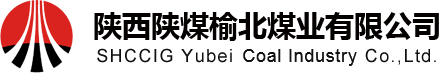

 榆北公众号
榆北公众号 榆北视频号
榆北视频号 榆北抖音号
榆北抖音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