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六下班那会儿,天还亮着,乌云刚退,空气里还带着潮气。我心里突然有点动静,像是被什么轻轻拨了一下,便转了方向,回了一趟外婆家。
车驶下高速那刻,我摇下了车窗。一股带着泥土和青草气息的风就这样扑面而来,混着湿热的空气钻进车里,也钻进脑子里。村口那棵歪脖槐树还在,风一吹,叶子哗啦啦地响,就像小时候外婆做饭时灶台下燃烧的玉米秆。
拐过几道弯,熟悉的老路尽头还是那座被槐树围着的小屋。门口的砖缝里长出新草,踩上去软绵绵的。橘猫早不若以前活泼,今天懒洋洋地蜷在门槛边,看到我,也只是伸了个懒腰,尾巴扫了两下,算作招呼。
屋檐下的饭桌早已摆好。臊子面的汤色红亮,羊肉热着,凉拌黄瓜切得细细的。外婆知道我爱吃酸辣,特地给我舀了一小碗渍韭菜,连芝麻盐都用旧罐子装着,像小时候那样。雨丝细细地落下,落在院落的青石板上,溅起一圈又一圈小小的涟漪。我坐着,看着这些熟悉的景物在雨中轻轻变换,积压的焦虑像雨水一样渗进泥土里。
饭后我顺着小路走出去,雨水还没干透,鞋底还沾着泥。田埂上的草疯了一样长,玉米叶被风掠过,“哗哗”响个不停。田里有几条小路,是人走出来的,但每年都变样,交错着,蜿蜒着,在日暮中延伸向远方,像那些已经模糊了的童年记忆,被新的脚印慢慢覆盖。
第二天醒来,屋里静悄悄的。小桌子上放着热好的早饭,小米粥冒着热气,鸡蛋饼软软地叠着。橘猫窝在椅子上,眼睛半睁不睁。我拎着碗出了门,才发现外公外婆已经进了地头。外婆戴着斗笠,一边掰“泽蒙”的花,一边喊外公别踩到嫩苗,说今年这一片能卖两万块钱呢,够交电费、买肥料,还能再存点钱。回屋时,她从裤兜里掏出几张保存的崭新的钞票,像掏瓜子那样随手塞我兜里,还低声说:“别乱花,城里贵。”我想笑,却有点笑不出来。那张钞票的边角是潮的,大概是刚才她摘泽蒙花时,手上还沾着露水——在她眼里,我永远是那个八岁时追着她喊饿,要吃鸡蛋饼的小姑娘。
下午要走了,外婆进后院摘了满满一袋豆角、辣椒,还塞了几个大小不一的南瓜。我推了几下,她摆摆手说:“城里买不到外婆种的这么好吃的。”语气里没有强求,像是早就知道我会拗不过她。
车发动的那一刻,我从后视镜看见他们站在路边,外公在整理草帽,外婆低着头,好像在拔草根。晚霞照在他们身上,把身影拉得很长,像两棵靠得很近的老树,彼此不说话,也不挪步。
他们不留我多住,只叮嘱我有时间回来看看,他们知道我有我该去的地方,就像他们还有田地、井水和晚饭要照顾。风从村子吹过来,带着晒干的泥土香,也吹上了我前行的路。(阳木生态公司 梁雅欣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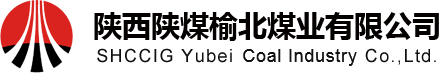

 榆北公众号
榆北公众号 榆北视频号
榆北视频号 榆北抖音号
榆北抖音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