陕北人做摊黄儿,不是什么稀罕事。家家户户都会,就像蒸馍馍、擀面条一样平常。可你要真想吃上一口正宗的摊黄儿,还得看婆姨们的手艺。
小米是主料,黄土高原上种出来的,颗粒不大但瓷实。头天晚上就得泡上,让米粒吸饱水,第二天碾起来才顺当。碾子一转,米粒就碎了,再用细箩筛一遍,粗的不要,只要那细溜溜的面。面调成糊,兑上老酵头,搁在暖和处,让它慢慢发酵。发好了,米糊会微微鼓起,闻着带点酸香,这时候就能上鏊子了。
鏊子是专门烙摊黄儿的家什,生铁铸成的,中间鼓,四边凹,像个浅碗。鏊子用久了,黑亮黑亮的,油光锃亮。火不能太旺,也不能太小,婆姨们烧柴火时,手一摸鏊子底,就知道火候够不够。拿勺子舀一勺米糊,往鏊子里一倒,只听“滋啦”一声响,赶紧盖上盖子。等上几分钟,揭开盖,米糊已经鼓起来了,金黄透亮,边上微微翘起,冒着热气。
这时候得赶紧用铲子铲起来,对折一下,摊黄儿就成了半月形。刚出锅的摊黄儿烫手,得晾一晾,可香味直往鼻子里钻,等不及的人就一边吹气一边咬,外皮微脆,里头绵软,甜丝丝的,还带着点发酵的酸味,越嚼越香。
摊黄儿原本是陕北清明节的专属美食,现在日子好了,啥时候想吃都能做。前段时间回老家见到一个老汉,蹲在窑洞前吃摊黄儿,就着一碗小米粥,吃得满头大汗。问他滋味如何,他只嘿嘿地笑,露出残缺的牙齿。那笑容比任何赞美都真切。
听奶奶说,以前谁家要是新娶了媳妇,婆婆头一件事就是教她怎么用鏊子。火大了不行,小了也不行,翻早了不成,晚了也不成。新媳妇手生,头几回总烙不好,不是焦了就是没熟透,自家男人倒不嫌弃,照样吃得香。做多了,手艺就练出来了。
鏊子凉下来了,灶火熄灭了,窑洞里飘着淡淡的米香。婆姨们用围裙擦着手,望着剩下的米糊盘算着明天的早饭。高原上的日子就是这样,简单得如同一勺米糊,却能在鏊子上摊开一轮又一轮金黄的月亮。
这月亮不照亮书斋画阁,只温暖着黄土坡上的一孔孔窑洞。(涌鑫公司:李韦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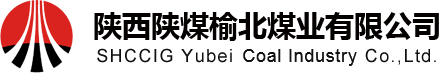

 榆北公众号
榆北公众号 榆北视频号
榆北视频号 榆北抖音号
榆北抖音号